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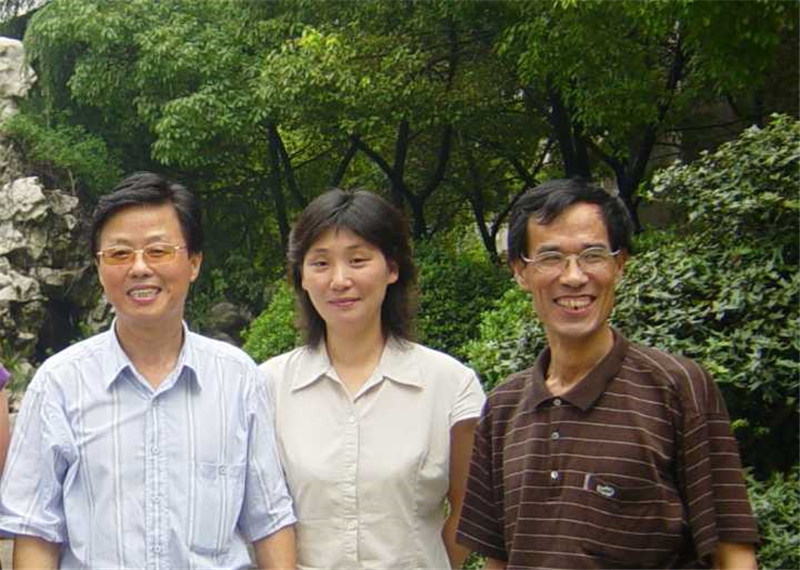
人与人的缘分是这么的微妙,我来三中后,先后有两个师傅——裴伯俊老师和蒋玉南老师。一位温文尔雅,自尊好强;一位心直口快,随意洒脱。两位师傅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他们对三中的教育都是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对我这个徒弟,他们也都是关怀备至。可惜的是,两位师傅都在退休后不久查出了身体问题,没过几年都相继离世了。回忆起我与师傅的那些往事,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1992年,我刚来到三中,裴老师是我的第一任师傅,当时的他已经是学校的工会主席了。对刚进三中的我来说,那时对师傅的印象还停留在开学的主持会议中他讲的第一句话,“教师是蜡烛”。因为他是用常州话讲的(因为在当时说人是“蜡烛”的话并不是褒义词),会场里响起了一片笑声。但对于三中来说,时间和事实都证明,裴老师的确是一支蜡烛,为三中的发展奉献良多。因为工作需要,不久后他就调走去校办厂做厂长,而在1998年的时候,由于体制改革,裴老师又回到了三中美术教师岗位,并且挑起了我们学校创建陶艺校本课程的重担。
我清楚地记得裴老师一心扑在学校的陶艺教育上,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他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让常州三中的陶艺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校园走向全省、全国,展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他促使了我校师生陶艺作品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学生制作的陶艺作品和老师撰写的论文多次在全国获奖;他执笔主编出版了由中央教科所审定的《陶艺》校本实验教材,让常州市第三中学成为挂牌的“江苏省中小学陶艺教育中心”。裴老师还经常应邀前往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进行讲学、师资培训。为此,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纷纷作了相关报道,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师生相继前来进行交流学习。特别值得庆贺的是,由中央电化教育馆、常州市电化教育馆、常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常州市三中联合编制,由市三中等学校教师示范,联合制作的《陶艺》电子影像教材(共八盘)被列入2005年全国中小学音像教材发行目录,亮相全国。国内有关方面的评价是,该教材是全国首部系统地介绍有关陶艺制作与教学的音像教材,所有的课例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及学科综合实践活动开拓了一条新思路。中央教科所郑旦华教授在德国发表的《陶艺教育在中国》一文中,对常州三中的陶艺教育作了相关介绍。这一切的成果都和裴老师的努力密不可分。
裴老师所做的一切我都全程参与了,还记得他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用电拉坯机,怎么上陶艺课,“逼着”我写教学反思……在裴老师的督促下,2006年,我的教学设计获得省教研室一等奖,写的论文获省年会一等奖。裴老师对我在教学和教科研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
裴老师他自己也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规划和设想,但是他不会用电脑打字(他执笔的文章多半都是我帮忙输入电脑的)。每当裴老师又要我去把文章打印出来时,蒋玉南老师就会跳出来替我“打抱不平”,要他拿到外面广告公司去打印。蒋老师经常“教训”我:“美术老师就要把字练练好!有空多练练毛笔字,不要整天只知道用电脑打印。”当他知道我报名去参加常州市第二届书法教师培训班的时候,蒋老师觉得我“孺子可教”,还特地刻了一个印章给我。
蒋老师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近20年,他率真随意,心地善良。记得裴老师为了我们的校本课程的编著,经常会弄到很晚才回家,有时都不能按时吃饭。蒋老师就会“讽刺”裴老师,“就是喜欢那些虚名”。他嘴上说着,实际却经常在裴老师的桌上放些小点心,方便裴老师饿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填填肚子。而他自己可能已经忘了,他在辅导高三美术生的时候,每天陪学生上完夜自修才回家,想方设法地找各种辅导资料,了解各类高考信息,晚上还帮学生带小点心,而自己在六楼上陪着学生画画,有时会忘记去食堂吃饭,所以干脆在办公室里放有整箱的方便面……蒋老师忘记了这些,而我却记忆犹新,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成为我日后学习的榜样。
我还在原来的办公室,从六楼向北眺望,曦园还是原来的曦园,只是树木长高了不少;东大道浓密的林荫把文化长廊给遮住了,当年筹建文化长廊的成员们——我的师傅裴伯俊、蒋玉南老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劲风过处,大树飘零,似乎在和我一同呼唤逝去的两位师傅!(文:朱冬健)
















 账号登录
账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