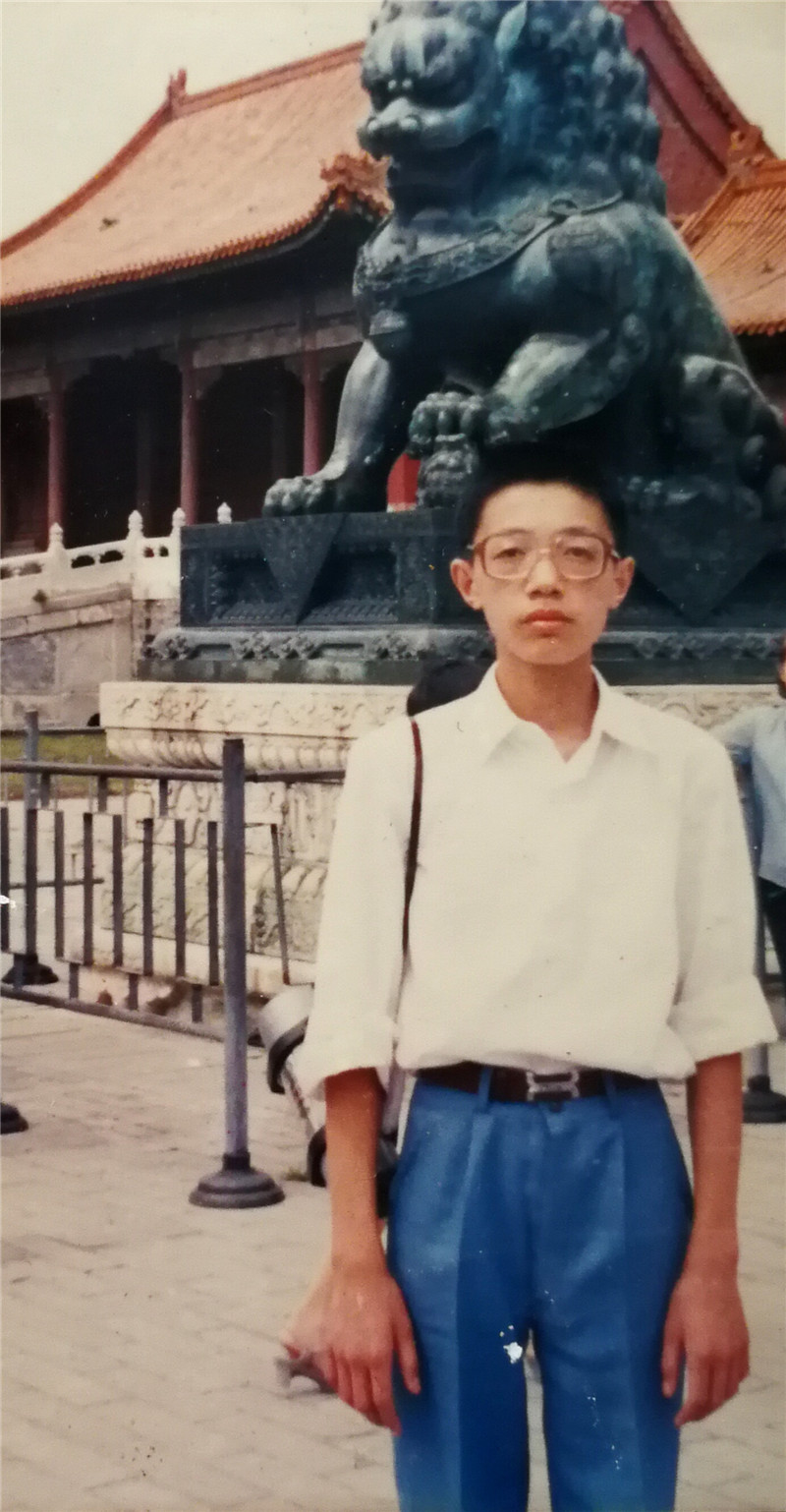
1985年金秋开学季,那年我13岁,骑了辆半新的常州金狮自行车,晃晃悠悠独自到常州市第三中学报到,从此开始了六年的中学生活。
依稀记得当年三中的模样,大门一侧是一排老旧的平房,那里是教工宿舍、体育部和食堂。再往里走,位于学校中央位置的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礼堂,只可惜这唯一具有艺术风格和文化底蕴的建筑,没能保存下来。大礼堂两侧分别是大操场和篮球场。绕过大礼堂,是高中部的教学楼,旁边是二层楼的行政办公楼,再往里就是初中部的教室,三排青砖大平房。
初中时光
懵懂少年,无忧无虑,感觉不到学习的压力,后来在老师们的教导下才渐渐地勤奋起来。
美术课是当年我最喜欢的科目。打小就喜欢画画的我,有幸遇到了裴伯俊老师,水粉颜料在调色盘中调和就画出了江南水乡的味道,水墨相融轻轻几笔就勾勒出活泼可爱的小鸡,运用焦点方法描绘出励志的立体美术字……在裴老师的课上,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美术知识,至今受益匪浅。
班会是我当年最喜欢的活动。记得初一时,班主任杨琴惠老师组织同学们开展了一次包馄饨主题班会,那可是同学们进入初中第一次热闹放纵。全班分成几个小组,男生负责带炉子生火烧水,女生负责做馄饨馅和包馄饨,各任课老师当评委。依稀记得当时各组女生包馄饨又快又好,但男生那边,手忙脚乱,烟雾弥漫,明显没跟上节奏,搞到最后有的组已在品尝美味了,有的组还在等炉火上窜,教室内外欢笑不断。也是从那以后,我掌握了一门手艺——包馄饨。每年的迎新年班会活动也很隆重热闹,记得上课刚刚结束,同学们就迅速将课桌围成一圈,拿出从学校附近炒货店买来瓜子花生,每人分一把摆在课桌上,鼓声响起,击鼓传花的传统游戏随之拉开序幕。随着鼓点,花球在同学们的手中飞快地传递,鼓停花止,至于表演的什么节目,已模糊不清了,但不管是中招的还是幸运逃脱的,都笑得前俯后仰,其乐融融。
午间是我当年最快乐的时间。那时由于路途较远,我和部分同学的午饭是带米到食堂蒸的。上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一响,食堂门外蒸架四周的人气顿时沸腾起来,一个个模样相似的饭盒,只能凭着盒盖上的红漆编号才能辨别,一双双手在蒸架上翻动、抽起,碰到饭盒盖子与饭盒分离的,保不准拿错了盒子,吃了别人的饭。饭后的午间基本不做作业,主要是在操场上自由“飞翔”。打乒乓是我的主要玩耍项目,记得大操场的南面围墙边有一排水泥乒乓台,中间没有球网,只能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红砖块排成球网,运气好的时候,一张乒乓台只有几个同学在排队;运气差的时候,不仅双打,还要和其他班的同学轮流混打,也许是受此影响,乒乓球比赛成了我最喜欢看的体育项目。
高中时光
1988年,结束了三年的初中生活,我没有参加当年的中考,直升至三中高中,那年我16岁。在那个迷惘的岁月,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学习渐渐成了永恒的主题。
高一,玩性未减,对学习还没上心。记得当时家里刚买了一部红梅牌照相机,我课余报名参加了学校摄影兴趣班。兴趣班指导教师是教政治课的徐诚卿老师,他除了写得一手好隶书,还是学校的摄影专家。一个夏天的傍晚,为了检验学习成果,我和另一位同学前往工人文化宫拍实景,选址、找角度、定光圈、按快门,将文化宫傍晚的景色全录入在胶卷里。后来,徐老师将我们带到学校他自行冲胶片的暗房里,昏暗的小屋里泛着红光,在显影液、定影液等化学溶剂的作用下,小水池盆中我们拍的底片渐渐显出影像,记得当时评价还不错,可惜底片没有保留下来,但摄影的基础理念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高二,心智逐渐成熟,选读文科。那年文理科分班后,我们文科班单独搬到了原教师办公楼一楼最西端,紧挨着围墙,沿围墙的操场直道正对着教室的窗户。由于学习任务紧张,课余时间几乎全被作业霸占了,后来连体育课都被主课占用了,上课时偷偷瞄着窗外操场上奔跑的身影,听着围墙外飘过来的卖甜白酒的吆喝声,成了放松心情的良药。再后来,开始上晚自习了,为了节省时间,绝大多数同学都带饭在学校吃,在当年的班主任姚兰萍老师的督促下,晚饭前在大操场跑几圈,成了我们劳逸结合的唯一活动方式,一段时期跑下来,居然治好了我的哮喘。
高三,疲于奔命地学习,迎接高考。那时的高三,已不上新课,整天泡在题海里,看到试卷都已麻木了。一天晚自习后,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回家,猛然发现路边开了家当时刚流行起来的台球室,从此周末放学和小伙伴玩几局台球,也算是当时唯一的娱乐项目了。那年高考实行预选制,未通过预考的同学后来也就不来学校上课了,教室里变得冷清了不少,高考前最后一天,下着大雨,去学校的路上积水很深,对面公交车开过,水花飞溅,一下子就超过了自行车的后座,为了避免摔倒,我只得将原本抬高的双脚放下,积水瞬间灌进了雨鞋。走进教室,鞋里的积水随着脚步发出响亮的吱咕吱咕声,引起阵阵哄笑,就这样,光着双脚踏在课桌底部的横栏上,我上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堂课。
此后,我告别了三中了,告别了最美好青涩的中学时光,走进了大学,当年我19岁,时间1991年。(文; 1988届 孙闽军)
















 账号登录
账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