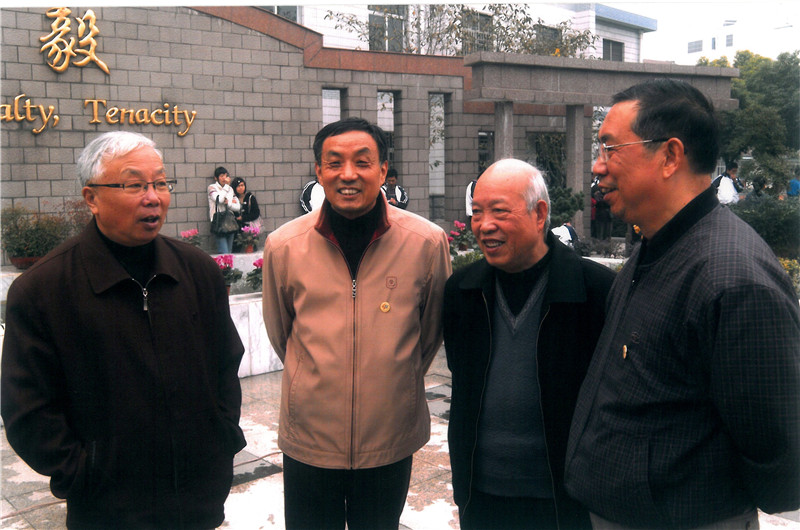
“辅华”——常州三中,我一生都会铭记在心中的母校。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我最美的初高中时光。后来我又在这里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整整七年。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李成立、汪瑞平等几位先生外,和我一样与三中有着这般亲密关系的人着实不多。冥冥中我觉得自己与三中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怎能忘记,我的青春,我的芳华!
一
1957年夏,我跨进了三中的校门,入学时我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每逢班上排队,我不是排头就是排尾,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屁孩,但学校却给了我这个小屁孩非常强的生长空间。
每天早读课之前和下午课外活动及以后,全校男女同学不需老师催促,几乎都会自觉来到校园内各处大小运动场所参加体育活动。跑、跳、掷;篮、排、足。人人都有爱好,个个都有擅长,“群体”活动真可谓“龙腾虎跃”“生龙活虎”。像我们这样的小屁孩受到极大的影响,下午课外活动,直至傍晚太阳落山时分都喜欢在操场上“疯”、“野”。
当时,高二高三的多位体育“明星”令我们这些小孩特别钦慕,至今他们的姓名和“形象”铭刻在心间。如蒋德芳,他家住在郊区,每天跑着上学、回家,时间久了就练就了一副铁脚板,成了长跑健将。往往他在操场上跑着,如我这样的小孩就在旁边一圈两圈地数着,他曾多次在市里的越野长跑中获得冠军。邹志华,高高的个儿,擅长田径,跳高1米64,三级跳远12米以上(当时这样的成绩是很骄人的,作为校记录恐怕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他进入了江苏省排球队,成了主攻手,退役后从事教练工作,直到当上国家男排主教练。我的同座,同样是小屁孩的朱志元,他的哥哥朱志泰却长得高高大大,尽管戴着眼镜,但他擅长跳远,纵身一跃就从沙坑的这一头飞到了另一头,在他身下的沙坑竟显得那样的狭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潘万诚的“大哥哥”,当时他是学校名副其实的百米飞人。每当他出现在校运会百米的赛场上,全校同学都会特别兴奋,都会把目光投向他;而他也总是不负众望,一次次地创造出好成绩,一次一次地打破校记录。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学校的春季运动会上,百米决赛将要开始,我大着胆子悄悄地挤到起点,当他把外衣脱下的时候,我就抢着把衣服抱在怀里,又挤到饮水处端了杯开水,来到终点。当他飞身冲过终点的时候,我赶忙送上衣服和开水,他一只手接过衣服,另一只手摸摸我的脑袋,说了声“谢谢”,顿时一股暖流充满我的心头。
说起我自己,我却很感惭愧。尽管我每天也跟着大家到操场上去“疯”,去“野”,但个头实在太小,体能实在太差,每当学期结束前,体育课上各项测试我总是不能达标。最后,总是麻烦体育老师与班主任商量,结果往往是“这个小佬,态度倒还好嘚,给个‘及格’吧!”
1958年下半年,一个喜讯传到学校,我校荣获由国家体委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体育运动红旗校”称号,其“含金量”非常高。据说江苏全省仅有两所学校获此殊荣。如这样重大的国家级的荣誉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整个常州市也是很难听到的。当那面红底金字,飘着长长流苏的超大锦旗被迎回学校时,全校师生拥向校园夹道欢迎,鼓乐声、欢呼声响彻校园,连学校周围的居民也自发拥来迎接。
二
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省常中在市里各中学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三中与一中、二中属同一档次,每年高考成绩此三校也总在伯仲之间,并无多少差异。三中有着良好的办学传统,稳定而又较好的教育教学质量,也有着令社会满意的信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有着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光是语文教研组就是有一批在全市有名望的老师。
陆逵先生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诲人谆谆,一派学者风度;朱小刚先生学养深厚,特别熟悉唐宋诗词,自己也能赋诗作词,平时不管是课内教学还是课外闲谈,言语中常会把经典诗句信手拈来,恰当运用,令人敬佩不已;周斌成先生生就的旅行大家,在旅游业并不兴盛的年代里,他就热衷于假日中遍游国内名山大川,并将丰富的见闻引进课堂教学,开阔了同学们的心胸和眼界。还有我曾亲身领教的岳德甫先生,听说他原来仅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自学成才,当上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写得一手见解犀利、文字冷峻的好文章。记得当时教师办公室前横排着一列壁报,专门用来刊登老师们的习作,岳先生经常在此发表文章。有一次,上课铃刚响,岳先生踱进教室,翘起大拇指指着办公室的方向大声说:“今天我又发了篇文章,你们课间前去读读!”一下课,我就和几个“活跃分子”一路小跑来到壁报前:“这是岳老师的文章吗?”“这文章放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堆里真可以乱真!”就是在这样的语文教学氛围中,我逐渐形成了对语文学科的兴趣,也为我后来一生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石。
其他各科的老师们也往往是才华横溢、一专多能的人师。杭甄先生化学科教得令各届学生称赞不已,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往往在上课前他就走进教室,摸出粉笔像毛笔一样挥舞,在黑板边缘写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样的名言,真可谓字字玑珠,引得同学们拍手称赞。有一次下课了,他索性自己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写下“龙飞凤舞”四个大字,同学们激动不已,有好几位同学拥到黑板前,用手指认真地描摹起来。金一鸣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物理老师,讲起课来条分缕析、清晰透彻,而且有声有色、活泼生动,这在物理学科的教学中是难能可贵的。课后,他到运动场上竟然能打一手好排球,“扣”、“传”、“垫”,样样在行,我们也就是从他的表现中开始懂得了一些排球知识。英语老师郑振荪先生,同学们平时只觉得他的言行举止怪怪的,也很有趣,想不到的是在一次全校文娱演出中他弹得一手好琴。音乐老师承子印先生当然是音乐教学中的一位高手,而他令我们惊讶的是从他那里我们才第一次领会到什么是“美声”唱法,那明亮厚实的音质真可称为“天籁之声”。太多了,恕我不能把每位老师都点到。总之,如这样一支教师队伍,这样一个出色的群体,怎么不会让社会、学生和家长信任呢!
三
时光荏苒,天赐吾缘,相隔近二十年后,1982年夏,我回到了母校,当上了一名语文教员,与其说是来当教师,不如说是再当一次学生。
当时,语文教研组由朱小刚、朱蜀安、王梦泽三位先生主持教研工作,组内有曹希白、巢云栋、周云龙这样知名的“大师”级老师,有王杏芬、沈祥珍这样正当年富力强、经验老到的老师,更有严晴秋、汪瑞平、曹韵、孙宪璋、谢建平、周志庆这样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老师(在我之后又引进了刘禾金、张新华、汪诚意、陈荣中等优秀老师)。全组同仁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他们对我的到来都持包容、欢迎的态度,从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很关心我、帮助我。
到校不久,随着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学校领导高瞻远瞩,牢牢抓住“课堂教学”这个主战场,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并决定以语文学科为突破口。这个决定得到语文组全体老师的积极响应,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学习,群策群力,人人为战,投入了“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和效率”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语文课堂教学出现了一派生龙活虎、面目一新的局面。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学校领导及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堂教学研究课。记得当时确定的研究课执教老师有严晴秋、汪瑞平,我也算一个。严、汪老师的研究课放在“现代文阅读”上,我则在“文言文阅读”上多做些尝试。我当时接连上了两堂研究课,课文分别是《过大孤山小孤山》、《六国论》。在课前的集备时,全组同仁围坐在一起,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研究课的主攻方向,是把文言教学中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老师串讲、学生听记的传统方法改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由学生自主地去朗读、理解、质疑、讨论的过程和方法,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老师则充分发挥组织、引导、释疑、检测的作用,从而师生共同完成教与学的任务。方向明确后,又对课文的具体内容,学生自主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教学实施的过程和方式都做了深入、细密的讨论和安排。待我写出教案后,全组同仁再次讨论审定,然后择班试教,评估结果。这种多次反复、集思广益的做法,充分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对充当执教者的我来说,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得到的帮助太大了。正式开课的时候,市区各中学都来了多位老师,省市教研室和《江苏教育》杂志社的有关同志也来了。课后,许多同志不仅对这两堂课,而且对学校的教改工作给予了肯定。回想起来,这两堂课对我个人业务上的提高和后来我所从事的教研员工作都有积极有效的作用。
我在母校从教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我学得了更多的待人处事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教学经验。就在写这段文字的此刻,语文组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又都一点一点地呈现在眼前;我把每一位老师一个一个地拨拉过去,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有和任何一位老师红过一次脸,顶过一次嘴。这种感觉真让我感动,以致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吧。
四
1989年夏,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母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与母校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到市教研室后,领导安排我分管高中语文教研工作,工作涉及面广,难度也较大,自己又须投入一个新的学习过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母校给了我更强有力的关爱与支持,以下两件事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一件事,当年,教研室领导要求各学科、各年段都要物色恰当的基层学校作为学科教研基地,我即刻就想到了母校。当我与学校领导联系时,学校领导当即就持欢迎的态度,这不仅是学校对市教研室工作的支持,也体现了母校对自己毕业的学生的爱护。在后来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市高中语文教研活动,每两周总要在三中举行一次。而三中从历任的校领导、语文教研组的负责老师,直到后勤方面的管理员工都关心和支持基地建设工作,从管理、学科教研、场所安排及其他服务各个方面都为全市的高中语文教研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基础教育曾掀起了一个教材改革的浪潮。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以周正逵先生为首的一些专家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分科型的高中语文教材:即将原来传统的文选型的综合课本改为分编的如“文学读本”、“文言读本”、“文化读本”和《写作》等分科型教材,并在全国布点使用。江苏省作为全国教育大省,常州市又是江苏基础教育的一大重镇,因此省教研室语文学科的负责老师给了我市选择一两所学校承担试教的任务。当时,我曾有倾向性地与多所重点中学联系,但大多数学校因担心“试教”会给高考带来负面影响而婉言谢绝了。这时,我又想到求助于母校。当时在学校主政的董小勋校长年轻而有胆识,他自己也是语文教师出身。他听了我的介绍,没说二话,立即就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认为采用这样新型的教材不会给高考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很可能还会带来积极影响。这样,三中就与武进奔牛中学成为我市的两所“试教”学校。学校经过认真的研究,确定了“试教”的班级与执教老师,并与我商量了双方合作开展一系列“试教”工作的举措。譬如安排了每周一次集体备课,定时定点定人(学校领导、语文组负责老师、试教老师和我本人),认真实施,从不间断。后来,原民进常州市委副主任、语文教学专家陈知义先生,时任教育局副局长、全省语文评优课一等奖获得者赵忠和先生也都来关心参与“试教”工作。我们还曾请人教社周正逵先生和省教研室朱芒芒先生来校督察、指导,也多次组织试教老师到外地外校去学习、交流、考察,最可贵的是试教老师很努力,很刻苦,从备课、上课,直到课后辅导等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惜付出地辛勤工作,平稳、顺利地完成了试教任务,获得了人教社的奖励,而后来的高考成果也确实没有受到不良影响。
絮絮叨叨,行文至此,总觉得言犹未尽,意犹未了。回顾往昔,我的一生真的始终与母校紧紧相连,这是很难以一段语言、一篇文字、几个片段的回忆能够表达清楚的。我还是引一首早些时候曾撰写的小诗来结束此文吧!
《赋赠母校辅华》
此生最念是辅华,
长吾之地成亦她。
诚毅校训明且真,
晨曦园土沃并大。
师长辈辈出俊彦,
桃李代代芳天涯。
心愿后侪更戮力,
传承开拓育新葩。
2017年11月于沪上(文:63届高中 蒋家义)
















 账号登录
账号登录